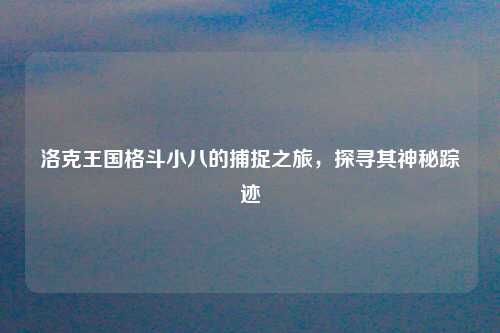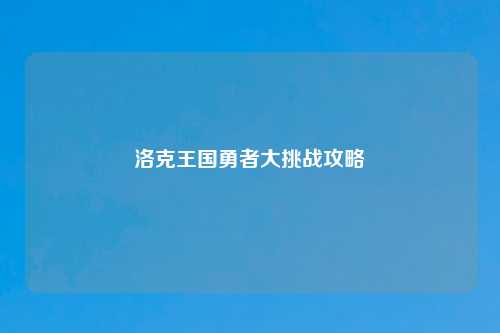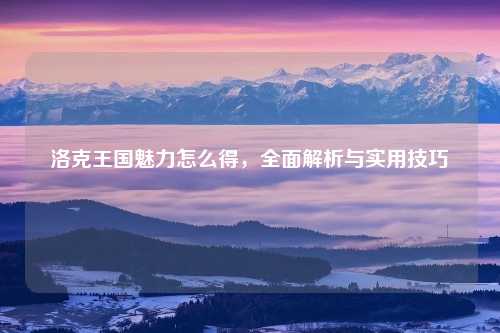头太元,为什么一个星期是七天
头太元,为什么一个星期是七天?
中國古易經就有七日來復
右图。七日来复。子夏曰:极六位而反于坤之复,其数七。日,其物阳也。京房曰:六爻反复之称。陆绩曰:六阳涉六阴,又下七爻在初,故称七日。日亦阳也。虞翻曰:消干六爻为六日,刚来反初,盖先儒旧传自子夏,京房、陆绩、虞翻,皆以阳涉六阴,极而反初为七日。至王昭素乃始畅其说,曰:干有六阳,坤有六阴,一阴自五月而生,属坤,阴道始进,阳道渐消,九月一阳在上,众阴剥物至十月则六阴数极,十一月一阳复生,自剥至十一月,隔坤之六阴,阴数既六,过六而七,则位属阳,以此知过坤六位即六日之象也。至于复为七日之象,是以安定曰:凡历七爻,以一爻为一日,故谓之七日。伊川:四七变而为复,故云七日。苏子曰:坤与初九为七。其实皆源于子午,夫阳生于子,阴生于午,自午至子,七而必复,乾坤消息之理也。故以一日言之,自午时至夜半复得子时;以一年言之,自五月至十一月复得子月;以一月言之,自午日凡七日,复得子日;以一纪言之,自午岁凡七岁复得子岁。天道运行,其数自尔。合之为一纪,分之为一岁、一月、一日,莫不皆然。故六十卦当三百六十日,而两卦相去皆以七日。且卦有以爻为岁者,有以爻为月者,有以爻为日者,以复言七日来复者,明卦气也。陆希声谓圣人言七日来复为历数之微明,是也。以消息言之,自立冬十月节至大雪十一月节,坤至复卦,凡历七爻。以卦气言之,自冬至十一月中气卦起中孚,至复卦,凡历七日。圣人观天道之行,反复不过七日,故曰七日来复。彖曰:七日来复,天行也。王辅嗣曰:复不可远也,夫天道如是,复道岂可远乎?岂惟不可远,亦不能远矣。

诸儒七日来复义
七日来复,彖曰:七日来复,天行也。王辅嗣云:阳气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以天之行反复不过七日,复之不可远也。孔颖达曰:阳气始剥尽,谓阳气始于剥尽之后,至于反复,凡经七日。案:《易稽览图》云:卦气起中孚,故坎离震兑各主一方,其余六十卦,卦有六爻,别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余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为八十分,五日分为四百分日之一,又分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别各得七分,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剥卦阳气之尽在于九月之未,十月当纯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尽则复卦阳来,是从剥尽至阳气来复,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举成数言之,故辅嗣言凡七日也。两汉诸儒传经皆用六日七分之说,故孔颖达述而明之,辅嗣论其大意而已。至于我国朝王昭素、王、宋咸始着论,驳之、胡旦明其不然。今录其语而弥缝其阙云。王昭素曰:注疏并违夫子之义,《序卦》云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以此知不剥尽也。况剥上九有一阳,取硕果之象,硕果则不剥尽矣。坤为十月卦,十月纯阴用事,犹有阳气在内,故荠麦先生。直至坤卦之末,尚有龙战之象,龙亦阳也。假使运有剥丧之时,则商王受剥丧,元良贼虐谏辅乃亿兆夷人离心离德,当此之时,岂无西伯之圣德、箕子之肾良乎?则知阳气必无剥尽之理。况阴阳者,刚柔迭用,变化日新,生生所资,永无尽矣。
胡旦难昭素曰:夫积阳则萎,凝水则载,男老则弱,女壮则雄,故蘼草死于始夏,荠麦生于孟冬,数已尽而气存。时已极而物反,天地之常理,阴阳之本性,阴之极有龙战之灾,故剥尽则复,穷上反下,皆正理也。言穷者,剥之尽也,言反者,复之初也,何知西伯、箕子非剥丧之人哉?昭素未之辩也。臣曰:阴剥阳尽而成坤,阴极阳反而成复,天之行也。以时言之,九月剥,十月坤,十一月复。以理言之,阳无剥尽之理,故坤之上六龙战于野,为其嫌于无阳也。上六则十月也。《说卦》曰:干,西北方之卦也,西北方亦十月也。序卦曰: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非特此也。五月一阴生,其卦为姤,积而成坤,故坤下有伏干;十一月一阳生,其卦为复,积而成干,故干下有伏坤。反复相明,以见生生无穷之意。盖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天地阴阳不可以一言尽故也。王胡达序卦之义而未尽夫说卦、变卦之妙,是以其论如此,然各有所长,不可掩也。
王昭素曰:注云至来复时,凡七日。注用凡字,取七日之义,即约酌而已,然未见指归也。疏引易纬六日七分,以十月纯阴用事,有六日七分。坤卦之尽,则复卦阳来。疏文此说未甚雅,当其六日七分是六十四卦分配一岁之中时日之数,今复卦是乾坤二卦阴阳反复之义。疏若实用六日七分,以为坤卦之尽,复卦阳来,则十月之节终,则一阳便来也,不得到冬至之日矣。据其节终尚去冬至十五日,则知七日之义难用易纬之数矣。
今论七日者,不离乾坤二卦天地阴阳之理。乾坤者,造化之本,干有六阳,坤有六阴,自建子而一阳生,至巳统属于干;自建午而一阴生,至亥统属于坤。
胡旦难昭素曰:西汉京房以卦气言事,皆有效验,东汉郎顗明六日七分之学最为精妙,夫卦之爻则实数也,岁之日则虚数也。岁月不尽之数,积而为闰,则加算焉。六日七分,实数也,三百六十五日有余焉,故算而为闰。昭素言从十月终至冬至,尚有十五日,未明岁月之积闰,术数之精妙也。惜乎!纬文丧失,京、郎已亡,学者难知,但凭臆说,后生穿凿,罕得师资,是以纷然而致论也。臣曰:昭素知九月剥,十月坤,十一月复,而不知此言,其大纲耳。坎、离、震、兑,各主一方,六十卦分主一岁,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凡三百六十日余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分于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气之进退推荡而成,如九月剥也,有艮、有既济、有噬嗑、有大过,凡五卦而后成。坤十月坤也,有未济、有蹇、有颐、有中孚,凡五卦而后成复。说卦言:坎,北方之卦也;震,东方之卦也;离,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于三卦言方,则知坎、离、震、兑各主一方矣,于兑言正秋者,秋分也。兑言秋分,则震春分、坎冬至、离夏至为四正矣。复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所谓至日者,冬至也。于复言冬至日,则姤为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可知矣。复彖曰:七日来复,则六十卦分主一岁,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可知矣。系辞曰:三百八十四爻当期之日,盖六十卦当三百六十日,四卦主十二节,十二中气所余五日则积分成闰也。大纲而言,则剥九月,坤十月,复十一月,故京房曰:剥复相去,三十日别而言之。复主冬至,冬至中气起于中孚,自中孚之后七日而复,故曰七日来复。譬如辰为天枢而不动,之处犹在极星之下,圣人之言居其所者曰北辰,而占天者必曰极星之下,详略异也。历代先儒唯玄能得其旨,故玄一中、二羡、三从、四更、五晬、六廓、七减、八沉、九成。中者象中孚之卦,冬至之节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律中黄钟,夏后氏之十一月也。其入牛宿之五度为周,周者,象复卦冬至之后周复也。宋衷陆绩曰:易七日来复是也。夫京房学于焦赣,其说则源于易矣。自扬子云、马融、郑康成、宋衷、虞翻、陆绩、范望并传此学,而昭素非之奈何?
王洙曰:孔颖达虽据《稽览图》以释王传,而易纬消息之术,月有五卦,卦有大小,有诸侯、有大夫、有卿、有公、有辟,五卦分爻,迭主一日,周而复始,终月而既,不连主,七日则是剥尽至复,全隔一月,恐王传之旨不在此义也。当以七为阳数,阴阳消复不过七日,天道之常也。凡消息据阳而言之,阳尊阴卑也。臣难王洙曰:辅嗣之意谓阳为阴剥,其气始尽,至于阳气来复之时,凡七日而已。何故如是?以天道之行,反复不过七日,复之不可远也。盖本于天矣。颖达以易消息之术考之,月有五卦,五卦分爻迭主一日,周而复始,终月而既,以成一岁,其六十卦之相去不过七日。阴阳消复,天道之常,则辅嗣所谓复之不可远也。其言验矣。孰谓王传之旨不在此哉?宋咸曰:卦气起中孚,如何?曰京房、郎顗、关子明辈假易之名,以行其壬遁卜祝、阴阳术数之学,圣人之,旨则无有焉。呜呼!好怪之甚也!文王、周公、仲尼悉以阴阳、刚柔、进退、消长、得失、存亡之象为之教云尔,又何以是卦直是月,是爻直是月云云之为乎?夫卦气何不起于他卦,而独起于中孚乎?臣难咸曰:六壬推日月行度,参以时日,得易之坎离者也;遁甲九宫八门,得易之河图者也。壬遁得易之一端,而不尽易之道,散而为阴阳术数之学易,亦何往而非阴阳哉?故曰:易以道阴阳,又曰:立天之道阴与阳,立地之道柔与刚,圣人推阴阳刚柔进退消长之理,为得失存亡之象,其道一。归于仁义而未始不原于天地。咸信进退消长而不信消息之卦,是终日数十而不知二五也。又谓诸儒假壬遁言易学以笼天下,不知壬遁实出于易,言易者亦何假壬遁哉?咸谓易书所不及者,为圣人之旨无有焉,且如河图洛书见于《系辞》,而河图四十五、洛书五十之数传于异人,安得以为圣人之旨无有哉?中孚,十一月之卦也。以岁言之,阳始于冬至;以历言之,日始于牵牛;以日言之,昼始于夜半;以人言之,虑始于心思。咸谓何不起于他卦,真不知者也。且不信直卦则阳生为复,阴生为姤,临至于八月有凶,八月不知果何月也。夫善味者别淄渑之水,善听者知要妙之音,善视者察秋毫之末,咸读易疏恶易纬之学而并废消息之卦,岂得为善观书者乎?刘遵曰:天行躔次有十二,阴行其六,阳行其六。当于阴,六阳失位,至于七,则阳复本位,此周天十二次环转反复,其数如此。施之于年、月、日、时并同,故一日之中七时而复,一月之中七日而复,一年之中七月而复,一纪之中七岁而复,今云七日者,取其中而言,则时、月、年从可知也。
胡旦难刘遵曰:一日之中从夜半至日中,一年之中从建子至建午,言其复也,亦以阴阳之数也。若一月之中七日,一纪之中七年,则未知阴阳之复如何也。若天之十二次环转反复,周而无穷,则未闻从玄至星纪。何者为阴,何者为阳?以寅、卯、子、丑言之,则天之十二辰也,其以子为阳,丑为阳耶?左转之也,与天戾矣。刘遵之论妄也。臣曰:遵论阴阳运行之数,得天道之行七日必复之理,但不本于乾坤二卦,消息之象以论之,是以其言近乎漫漶,要之亦有所长,未可斥之以为妄也。夫阳生于子,阴生于午,自午至子,七而必复。以一日言之,自午时至夜半而复得子时;自一年言之,自五月至十二月而复得子月;以一月言之,自午日凡七日而复得子日;以一纪言之,自午岁凡七岁而复得子岁。天道运行,其数如此,合之为一纪,分之为一岁、一月、一日,莫不皆然。故六十卦当三百六十日,而两卦相去皆以七日。圣人所以存其七日来复于复卦者,明卦气也。陆希声谓圣人言七日来复为历数之征明,是也。王洙曰:凡阴息则阳消,自五月至十一月,其日之历行天七舍,而阳气乃复。故云七日来复。复初体震,震居少阳,其数七,复则君子道长,因庆之也。庆在乎始,其言速,故称日,取乎日行一舍也。臣难王洙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八舍,日行一度为一日,行一舍与月合朔为一月,洙取日行一舍,故称日,盖用褚氏、庄氏变月言日者,欲见阳长之速,大同而小异。要之日行七舍,自是七月,安有变月言日之理?且如诗言:一之日,二之日,止是省文,葢言十一月之日,十二月之日也。
王昭素曰:干有六阳,坤有六阴,一阴自五月而生,属坤,阴道始进,阳道渐消。九月虽有一阳在上,无奈众阴之,之剥物也。至十月则六阴数极,十一月一阳复生,自剥至十一月,隔坤之六阴。六阴盛时,一阳自然息迹,阴数既六,过六而七,则位属阳,以此知过坤六位,即六日之象,至于复,为七日之象矣。
胡旦难昭素曰:易纬以剥卦阳气之尽在九月之末,十月纯坤用事,隔坤一卦六日七分,阳气来复。昭素以五月一阴生,至九月虽有一阳,无奈众阴之剥物,至十月六阴数极,十一月一阳复生,此则谓昆为兄,窃褚庄之美为己力者也。臣曰:昭素虽掠褚庄之美,其论乾坤消息阴阳六位周而复始,得易之象。虞翻、陆绩推六十卦以解太元八十一首,于中言象中孚,于周言象复是,于六日七分卦气之学既笃信之矣。而翻注七日来复曰:消干六爻为六日,刚来反初,七日来复,天行也。绩注京房易传曰:六阳涉六阴,反下七爻在初,故称七日。日亦阳也。岂唯虞陆之学如此,论六十卦者京房也。而房作复传曰:七日来复,六爻反复之称,葢天地之间有是理则有是象,有是象则有是术,其致一也。故子夏曰:极六位而反于坤之复,其数七日,其物阳也。安定曰:凡历七爻,以一爻为一日,故谓之七日。伊川曰:七变而为复,故云七日。苏氏曰:坤与初九为七,皆言七日之象也。易之为术深远矣,故鼎祚于此请俟来哲。若陆希声、刘牧王洙、龙昌期以七为少阳之数,则无取焉。
一曰策数,二曰爻数,三曰卦数,四曰五行数,五曰十日数,六曰十二辰数,七曰五声十二律数,八曰纳甲数。
少阳七 二十八策
老阳九 三十六策
少阴八 三十二策
老阴六 二十四策
右策数者,四象分太极数也。震勿逐,七日得。仲翔曰:少阳七即此二十八策也。讼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曰:干为百,坤为户,三爻故三百户,干一爻三十六策,三阳一百八策。
震彖曰:震惊百里。曰:阳爻三十六,阴爻二十四,震初九、九四,二阳二阴为百二十,举其大数也。陆希声疎矣。
本文取自易学网。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
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为什么要娶姨母?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是个狠人,十五岁建立北魏先不说,光是干掉姨夫,娶了小姨就足够称得上狠人了。
拓跋珪本是代国皇子,但在他五岁的时候代国灭亡,他的母亲贺兰氏带着年仅五岁的拓跋珪逃往匈奴独孤部。
经过十年时间的沉淀,当初那个连剑都拿不稳的拓跋珪已经有了不小的名气,更是敢于抓住机会,在东晋兵败的时候顺势起兵,带领一群鲜卑族的旧部重新建立了代国。
建立代国后,由于拓跋珪非常崇拜三国时期的曹操,于是就索性将自己国号从代变为魏,史称“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被后世称为“北魏道武帝”
拓跋珪在建立北魏后就开始进行南征北战,誓要统一北方,在拓跋珪的努力下,北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强大起来,为后来拓跋焘统一北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拓跋珪的功绩上看,确实是一位狠人,从生活方面看,他也是一位狠人,这怎么说?
有一次拓跋珪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妹妹,也就是自己的小姨,实在是惊为天人,然后就想娶她回家。
不过这件事遭到了母亲的拒绝,理由是你小姨人家有丈夫,你现在求亲实在不妥。
可拓跋珪是什么人啊?狠人啊!结了婚有丈夫又如何?于是拓跋珪直接带人杀了自己姨夫,将自己小姨给带回了家,并让他给自己生了一个儿子。
至于拓跋珪为什么非要娶自己的小姨,其实原因很简单,前面也交代了,就是因为小姨长得好看嘛,红颜祸水谁不喜欢?
并且拓跋珪也并不是一个禁欲的主,在拓跋珪晚年的时候就开始沉迷于酒色当中无法自拔,最终也是因此被刺死宫中,可见抢小姨是在意料之中。
拓跋珪抢小姨这件事在现在看来属实令人难以接受,但在当时虽然引起了一时的轰动,但没过多久就平息了,就好像这事完全不重要一样,这是为何?
人口稀少
这就不得不从古代的社会情况说起了,古代由于经常发生战乱,所以人口非常稀少,而一个国家想要强大就必须要有大量人口。
于是朝廷就想到一个办法,鼓励青年们娶寡妇,也鼓励自己兄弟娶已经成为寡妇的婶婶或者嫂嫂。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口果然有所提升,而至于什么伦理道德,在当时完全没有这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拓跋珪只是做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能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为了娶小姨,甚至把姨夫给杀了,这才是轰动的点。
文章结尾,让我再说一句,拓跋珪真乃狠人也!
感谢阅读,如果觉得文章不错,就给文青点个关注或赞吧,感谢大家~
(网络配图,侵权删除)
能分享一些古代女子发型图吗?
这五十张q版古代女子发型,你喜欢哪个呢?👏😁古代女生的发型图片,我只分享图片,不介绍哦(;`O´)o因为前面几位介绍的想当详尽了!
q版古代发型好漂亮呢!大家随意看看欣赏也很好哦😊哦
大头儿子叫什么名字?
大头儿子这个名字是虚构的,没有具体的名字。因为大头儿子是一个动画片中的角色,是由动画师创作的人物,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不过,大头儿子在动画片中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和特点,他勇敢、乐观、聪明机智,同时也有一些缺点,比如有点懒惰,有点自以为是。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观看动画片来了解大头儿子的种种特征和故事情节。
历史上的孙权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前提是充分了解和掌握该人物所处的历史阶段,时代背景和生存环境。一个具体的、有资格被后人评价的历史人物,几乎注定是复杂的。对其越不了解,做出的评价就会越抽象,越简单。最后归结到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这种评价已经说不上和本主有太多关系了。
说回孙权。在三国三位君主中,孙权的寿命最长,但存在感最低。曹操和刘备的专业著述都很多。但像样的《孙权传》至今还没有一本。即使是东吴方面的拥趸,关注点也往往在江东文武卿相身上。孙权反倒成了功能性的角色。真正设身处地地具体的关注,并不多。举例子说,“孙权年轻时候颇英明,可惜晚年昏庸”这是很常见的一个评价,但这个评价就忽略了孙权年轻至晚年时决策的具体环境。所以, 不能说不对,但也没什么用。
以我的观感,评价孙权,至少需先关注以下几点。
一、孙权的第一身份,不是东吴的帝王,而是孙家的家主。
二、江东孙氏以武得国,素无恩义,与部分江东土居士族甚至有着深刻的难以弥合的矛盾。
三、东吴政权是在汉末群雄割据背景下相继淘汰后的残存。
四、相对曹魏和刘蜀,东吴政权天然不具有合法性。
这四条相互作用,决定了孙权必须是生存主义和投机主义者,其他任何选择都不足以让他撑住孙氏的家业,并且维持东吴政权的相对稳定。从这一点出发,孙权的从少至老的行事逻辑,其实相当明确,而且极少改变。
孙氏取江东,根源于武力的强力镇压,此所谓以武得国,前贤多有论述。孙权的继位,缘于孙策的暴毙,实际上是意外。孙策死时26,而已有子。哪怕他能活到46,孙家的家主也不可能轮到孙权。所以孙权之前实际上并没有作为江东储君培养的过程。设若孙策不死,孙权将来的处境,只能是又一个孙静。所以孙权继位之初,既少核心班底,又缺乏当然的合法性。最后虽在张昭、周瑜的拥护下站稳脚跟,但仍经历了孙翊、孙暠、孙辅等诸重竞争。正位实属不易。而其时江东地只数郡,内外不靖,强敌环伺。居然还有阴谋论认为孙权谋害孙策只为争位子,得是多2才想得出来?
孙权既正位,以下就要考量他本身的素质。孙权的文治,未必过于孙策(孙策似暴虐,而孙权仁善,究其根本,均是具体实势下不得不为之的表现。孙策以客军侵境,攻杀大姓,不暴虐何足存身。但既已立足,欲求长远发展,自会转为仁善。孙策死前,已有相当程度的缓和举措。这是政治人物自然的抉择,非只个人性格),但军事则远逊孙策。本来孙氏诸子中,孙权也不是突出的将才。但孙氏以武得国,武力是孙氏权力的凭籍,要害中的要害,太阿权柄,绝不可假手于人。孙权对这一点当有深刻认识,而实际上才能又不足,这是孙权一生杯具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素。
此后数年,江东相对平稳。孙权一边苦练内功,一边内平山越,外打黄祖。打了N年轮了N次,其时被后世吹得神乎其神的周公瑾诸人均在。可见江东“外战外行”这帽子不能扣在孙权一人身上。是时孙权与刘表的表现,并不比两川张鲁刘璋的争斗更加精彩,也还看不出天命之所归。
而转折在赤壁之战。此战的成功,有许多因素。刘备方的联盟与辅助,曹方的轻敌,天气、疾病乃至江东文武并力,将士用命。而战后对孙权最显著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极大程度夯实了孙权的统治基础。尽管孙权没亲自上阵,赤壁是他一生最大的武功,足以压服其他任何异见者。之前,鲁肃见孙权,便以帝王大业劝之,而张昭视为狂诞。张昭还算是孙权阵营比较核心的人物,则江东本土态度不问可知。但在赤壁之后,就很少人怀疑这一点了。
然而层次的跃升,是对能力的更大考验。此后孙权一跃直接与曹操、刘备这等级数相较。后两者都是久见山陵变化,人老成精的人物。经历和阅历都远过孙权。孙权不是对手,也不全由才智不逮。实在是时势所迫,不得不提前进入不对等状态。结果在赤壁战胜余威之下,被刘备一连串开挂式的组合拳打得懵头转向。孙权和刘备,在同盟关系之外尚有互相竞争。而外交的后盾,归根结底还是武力。
然而孙权自己军事不行,只能寄托于武将。其手下最有大将范儿的周瑜周公瑾建安十五年英年早逝。鲁肃不长于战阵,吕蒙还不够成熟,一时青黄不接。以致赤壁战后,江东并未再有规模性的大胜。期间孙权不安于室,亲自领兵去打合肥,得到称号“孙十万”,成就了张八百的美名。这一战对孙权心理的打击,甚于损兵折将。此后他该亲征还是亲征,但对自身军事水平的自信却一去不复返,而转为对吕蒙一代新兴将领的期望。
到了建安二十四年,吕蒙一代已经成型。即吕蒙对孙权陈述的吕蒙、孙皎、蒋钦、潘璋四将,年龄、能力、忠诚均可圈可点。以此为重心,集合前后新旧诸将,已成战力。又值关羽北伐,遂袭取荆州,是为孙权一生第二大武功。然而天灭孙权,建安二十四年大瘟疫中,四将一下挂了仨。这对孙权的打击空前绝后。即使孙登去世,两宫争衡,均不像这样突如其来,孙权毫无准备。袭取荆州以后,孙权的举措混乱投机,令人齿冷,早想什么去了?其实就是孙权多年苦心预备好的武将班底被老天爷一下整没了的缘故,换谁谁也受不了。
孙权自己军事不行,多年经营非战之罪一朝覆没,而刘备又大起问罪之师,无奈之下,才起用江东士族背景的陆逊。自建安五年继位以来,孙氏以武得国的权柄,首次外假于江东士族。而陆逊偏偏获得大胜,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东吴作为一个政权的覆亡,要到很多年以后。但孙氏的中枢权柄,从夷陵战后就动摇了。
此后孙权的种种看似倒行逆施,比方检校案,比方太子失宠,比方两宫争衡,乃至南下夷洲,北连公孙,一切的作为都是为了把已动摇的权柄再次确立回来,而始终不得如愿。孙权与陆逊的外和内争也贯穿了陆逊的一生。而孙权的态度,也自然从前期的进取转为后期的消极。 所谓今日之忧,不暇及远,此子孙事也。到了东吴后期,世家大族再次崛起,江东孙氏,已不过是满朝冠冕之上的虚景浮云。
所以,该如何评价孙权呢?
第一,这是一个苦命的人。第二,这是一个杯具的人。第三,这是半个英雄。
仓促继位,处危难之境,居嫌疑之地。有英雄之志,处英雄之世,居英雄之名。而能力未荷。倘在承平之世,从容继位,亦可成为明主。但肩负重任,无法选择,面对强敌,屡败屡战。人只见其败于军事,而不见其败于内政。爱醇酒,爱行猎,爱繁华,而实虚弱,实无助、实孤独。赤壁之后,每次奋斗都归无用,每次努力都成笑话。不肯当配角,又没主角命。后世一曰孙渣,一曰孙十万。
这就是孙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