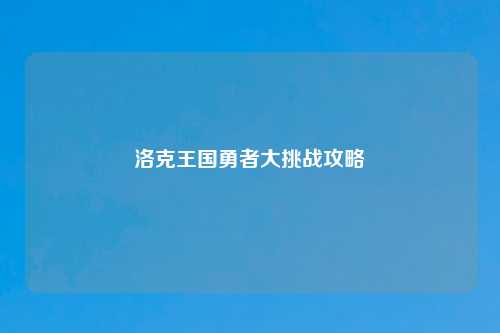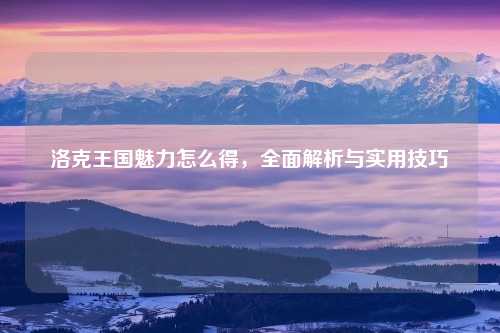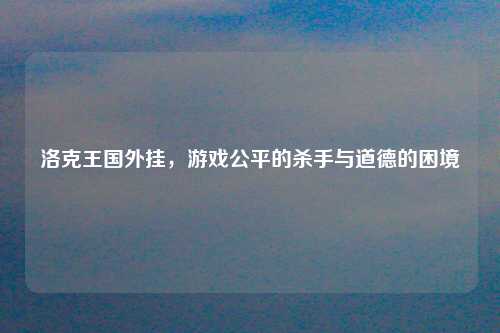2017夏日套,安安静静许某怎么做到的
2017夏日套,安安静静许某怎么做到的?
许某某怎么做到安安静静,不惊动邻居,把来女士送走的呢?根据我的分析,他大摇大摆的从摄像头下有过,都不会有人知道他是在干什么。
杭州警方在7月25日上午10时,直播通报中回应网友热线话题,前期网传“许某某是侦察兵退役”、“许某某在小区物业工作”、“许某某熟悉小区和楼道的监控死角,刻意躲避监控”和“许某某利用隔壁空置房进行分尸”等等说法,均与所查证事实不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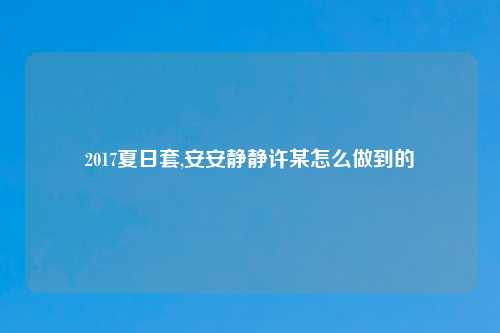
警方通报经过审讯,7月23日10时,突破了许某某的口供。许某某初步的交代,因为家庭生活矛盾对来某某产生不满,于7月5日凌晨在家中趁来某某熟睡时,将她杀害后并分尸扔至化粪池内。杭州警方在直播中还通报道,自1987年开始许某某先后在省内外多地从事鱼粉和养殖生意,然后2018年才来到杭州工作。
得到以上这些消息,要分析许某某怎么做到不惊动邻居就把来女士送走,这就不难了。警方通报中报道,经过审讯许某某交代他因为家庭生活矛盾对来某某产生不满,于7月5日凌晨在家中趁来某某熟睡的时候,将她杀害并分尸扔至化粪池内。
而许某某1987年开始先后在省内外多地从事鱼粉和养殖生意,2018年才来杭州工作,按时间推算,有31年的从事养殖和鱼粉工作,这方面就难以避免会有杀鸡鸭,杀鱼之类的了,这充分说明对处理尸体他是有一定的经验的。
充分的准备,和过硬的心理素质,加有一定的处理尸体经验,对于一具100来斤的尸体进行处理花不了多少时间,根据本人查看了杭州近一个月的天气预报情况,杭州7月5日是有中雨,他可能就利用了下雨的雨声做为掩护,无声无响的杀害了来女士,再进行分尸,而且动作比较轻,所以女儿和邻居没有察觉。
据说60平米的房子主卧是没有卫生间的,他杀害来女士以后可能就是在房间内进行分尸,因为他可能担心女儿突然醒来发现,要对尸体进行分尸前找用彩条布铺垫地板,防止留下痕迹。之后可能将部分软小部位冲入卫生间,彩条布也剪碎冲入,其余骨头硬物,拿到小区化粪池去扔,在警方通报他的口供中也是说拿去化粪池扔的。
那么问题来了,他是怎么把剩余的尸体无声无息的运出去呢?这尸体怎么运出去警方并没有做详细的介绍,好奇的我们只能我们自己推论了,总之规避摄像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他是利用外出买菜,和送孩子上学的时间把这剩下的尸体部分,分批次,分量的利用透明胶绑定自己大腿以及小腿之上,然后穿长着裤子,利用裤子的遮挡,正常的走出去处理丢弃的。
因此他暂时的瞒过了邻居瞒过了大家伙,把来女士杀害并分尸处理,但在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胜利永远属于正义的一方,最终他还是难逃法网。
可怜的还是他们的小女儿,成为了孤儿,一辈子都有爸爸杀妈妈的阴影,据说7月5日那天正好是她12岁生日,还是未成年人,监护人该是谁?
跟姐姐?在姐姐眼里她爸爸害死了妈妈。跟哥哥?
在哥哥眼里,都是因为她妈妈,爸爸才犯罪。
可怜的孩子,难啊。
以上内容纯属本人个人观点,准确消息以官方通报公布为准。
认同内容观点的朋友帮忙点个赞,转发一下,谢谢。你见过哪些深藏不露的高人?
在幸福二村,我的书法师傅张荣魁老先生家里,碰到一位师傅的邻居,自言姓余,让我称呼他余大爷。
其实我背后经常称呼他老余头,因为我觉得他有些为老不尊的样子。
比如我们俩一起下围棋,他会趁我不注意偷偷挪动我的棋子,尤其是在局面上胶着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莫名让对方做活了棋眼,从而有了扭转败局的机会。
一次两次我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异常,还以为自己确实就是棋差一招,技不如人,乖乖弃子认输。
后来次数多了,引起我的怀疑,仔细观察后发现他用胳膊做掩护,偷偷私底下重新排兵布阵。
我说余大爷您不讲究,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不怕晚辈笑话?
老余头笑笑一脸不在乎,还振振有词说什么“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等等自以为是的托词。
我只好威胁他说余大爷您要是这样不讲江湖规矩,以后我可不和您下棋了,我不伺候了。
老余头就会急赤白脸,说“别呀,你娃水平还可以,比那个小木匠能耐多了”。
老余头嘴里的“小木匠”就是我的书法师傅张荣魁老先生。怹退休前是八级木工,和当时的一位领导人是师兄弟。
张师傅经常说起的最为自豪的两件事就是参与过天安门广场上两个建筑物施工,另外则是他的位居高位的师兄,最后也只是七级木工,没有达到他八级木工的天花板。
老余头则讽刺张师傅说张师傅的八级木工只是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而他的位居高位的师兄,早就是高级知识分子,比张师傅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张师傅说别的“相当于”我不和他比,我们俩的老恩师教给我们的就是木工手艺,我只和他比木工。
一句话噎得老余头说不上话来。
老余头这人非常奇怪,不是那个小区的原著居民,几年前突然搬到那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子里,没有老伴,也没有看到有儿女来探望照顾,就是一个人生活。
老余头会好几种外语,我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发现的这个秘密,因为他平时从来不说外语,也不说自己懂外语。
我当时有一项技术发明要申请专利,自己准备提交资料,我先是自己把中文资料准备利索,装在一个文件夹里,拿着去张师傅家顺路看看他,老余头当时也在。
张师傅埋怨我说又忙什么呢,有些日子没来了。
不愿意谈太多工作上的事,我就把手里的文件夹递给他们,说这不是忙活这件事吗,这还是插空过来的,英文版的还没有准备齐呢。
老余头拿过文件夹,打开看了看里面的资料,说专业术语我不太有把握,如果你把专业术语给我补充一下,我几分钟就给你翻译过来。
我有些诧异说余大爷您还懂英语啊?
张师傅说您余大爷会的东西多着呢,不但会英语,还会日语、法语、俄语、德语、斯拉夫语。
又转过头问老余头,你还会什么语?
老余头说阿尔巴尼亚语简单会话也没有问题。
我说余大爷您行啊,高人啊!深藏不露啊!
这时我突然有一个疑惑,没有走脑直接问出来:
余大爷,您老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老余头打哈哈说,东搞搞西搞搞,也没有正经干过什么工作,瞎混了大半辈子。
我知道他的档案里说的是从老玉石加工厂退休的工人,可是那个厂子早就破产了,职工早就分流干净,原厂址都建成了公园。
当然我说的这个档案是他自己提供给居委会的个人情况简述。
那天老余头一边口译我一边记录,关键的专业术语我就补充几个词,很快完成了英文版翻译。
我突发奇想说余大爷您再给我用法语翻译一遍,我觉得法语特别好听。
老余头说你就是吃饱了没事干撑得,什么时候请我喝酒我再给你说。
其实我经常请张师傅和老余头吃饭喝酒,每次过去一般都是请他们吃顿饭我再走。
我们当时喜欢在幸福二村附近的“渝信”吃饭,喜欢那里的氛围,不像传统的酒楼,进门就是大堂,里面的食客沸反盈天。走进渝信,静悄悄的,没有大堂,食客都在楼上包间。
老余头应该酒量极好,虽然他每次都是三两多酒,再劝就以年龄大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可是他喝那三两酒的样子,像极了张飞对付一盘豆芽。
我业余时间跟着张师傅研习书法,平时聊天自然经常谈起诗词歌赋。张师傅说自己虽然木匠出身,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对于书法创作过程中的引用,还是讲究文化内涵和书写准确,不能有疑义,更不能有错别字。
老余头的文学修养非常高,唐诗宋词张口就来,国外名著也是说的头头是道,往往还有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对于莎士比亚的作品,能够大段大段背诵原文。
不知道大家读没读过英文原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奥赛罗》、《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等这些莎翁的作品,那些作品中的英文单词和语法,和我们现在学的单词和语法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按着我的英语老师的说法,那是英文的古文。
能够大段背诵那些东西,我愈发认定老余头不是一般人。
我当时上学时学的机械制造及系统优化设计,研究方向是智能化机器人,对于弱电及微电子以及信号理论知识也有深入的学习,喜欢琢磨传感器应用方面的问题。
即使说到这些纯工科的内容,老余头也是对答如流,应付自如,而且在短波信号发射与接受方面,见解独特,也能听出来实践经验丰富。
老余头已经六十多岁,六十五六的样子,微胖,秃头,每天精神抖擞,乐观豁达,除了和我下围棋,总是乐呵呵无忧无虑的样子。
有一次,冬天,我去幸福二村看张师傅,走的是东边那条长胡同,看到巷子里停着一辆黑色的奥迪,车牌比较特殊,像是特殊部门专用。
看到老余头,在两位年轻人的陪同下,走出小区,上了汽车。
那两位年轻人,穿着普通人一样的黑色皮夹克,留着平头,一身行伍之气。
巷子窄,两辆车不能并行,我犹豫着要不要退回去,看车牌我有点不敢惹。
还好,奥迪倒车,在公厕旁边的空地上甩尾,北行汇入干路。
到了张师傅家,我问张师傅老余头干什么去了,来接他的是什么人?
张师傅说老余头去例行体检了,接他的人不认识,每次都是那几个人,来了后不怎么和别人交流。
有一次我和老余头说起某高校有一位义务传授形意拳的老师,自言是正宗传人。
老余头一撇嘴说他们瞎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再后来,我因为工作调动,有几年没有去张荣魁师傅家看他,电话里交流时又说起老余头,张师傅说老余头不在幸福二村住了,说是搬去了什么疗养院。
我和张师傅开玩笑说师傅您和余大爷交往好几年,到底您俩谁大?
张师傅说我怎么会知道,老余头嘴里没准头,档案上他69了,比我大,他又说自己才65,又比我小。好在我们一直都是老余头、老张头这么叫,也没有特别论谁大谁小,我甚至不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姓余。
我不禁想起有一次我们三个去燕莎附近的凯宾斯基吃西餐,老余头随意挥舞着刀叉,比我这用了几十年筷子的人使用筷子还要熟练,一些吃西餐的所谓礼仪也特别到位,完全不像穿着老头衫摇着蒲扇的胡同大爷的样子。
我笑着和张师傅说:
老余头该不会是无名英雄吧!
没想到张师傅却斩钉截铁说:
应该就是!
你见过的渣男有多渣?
恋爱五年敌不过认识一个月的,只因为她家里……,我朋友的真是故事,这算不算渣??
你身边最性感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露肩
露背
牛仔裤超级百搭,这种露腰的上衣尽量不搭太娘气的裙子(娘man平衡一下
还是露肩
露肩毛衣春秋单穿或者冬天打底都很棒!
有腰显腰!
帽子和choker都是平衡娘man的利器!
穿衣服搭配尽量上下不穿同一种风格,比如上衣穿露肩,下半身就搭比较休闲的,尽量避免上衣紧身露肩还搭个紧身裙这样,再搭配饰品发型。
穿吊带记得脖子上戴东西
秋天可以西装外套搭开叉的连衣裙露出腿
冬天可以在内搭和配饰上下功夫,外面套着大衣,到了暖气房做精致的猪猪女孩。
珍珠项链搭配紧身v领
颜色比较艳的v领
娘man一下,可以在这种小外套里塞羽绒服,天气不是很冷的时候里面穿吊带也OK,我穿了运动短袖。
紧身高领紧身牛仔裤
偷偷加一张,其实平时我是这样的。
看到这么可爱的我 大家看完记得点赞好嘛不要看完就溜啊☺️☺️
古人为什么穿开裆裤?
现代人为什么穿破洞牛仔,古人就为什么穿开档,合裆裤出现之后依旧没能阻止中原人传开裆裤,古人似乎对开裆裤有种执念,清朝晚期依旧广泛使用。
裤子最早是穿在里面,秘不示人的亵衣裤,也称作袴、绔,其实早期的中原先民们根本就不穿裤子,而是用兽皮之类裹着下半身,但是这种穿着夏天还好,到了寒冷时节就难以忍受,因此,人们用两条管状的皮毛或者布帛制品裹住双腿,从脚踝到向上,用于保暖,这就是最早的裤子。
由于裤子一开始发明出来的时候,向上只到膝盖,再往上的部位就没有了遮蔽,因此当时都是上衣下裳与袴三者共用。
《易经》: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虽然衣裳在现代通常合称,但在古代,衣和裳的分开的,指的是上衣下裳,也就是上半身的衣物与下半身的裙子,古代无论男女,穿着都是如此。
从上古时代开始,上衣下裳的制度就逐渐成熟,到了周朝成为主流,而裤子,只是当时作为内衬用于冬天保暖,并非是主要的衣物构成部分,而且穿在里面,外面被裳遮住,所以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只有高贵的人,才坚持穿开档中原的先民们,一直坚持上衣下裳的服制,然而这种服制也有问题,那就是不太方便,尤其是天气太冷或者太热的情况下做事的时候,穿着太闷,不穿不行,虽然冬天会使用袴,但是终究只能遮挡腿部的一部分,还是受不了。
更麻烦的还是作战的士兵,尤其是骑兵,穿着开档骑马什么感觉可想而知。
而中原一直穿着开裆裤的同一时期,漠北与西域的游牧族群,已经制成了与现代几乎无二的合裆裤,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军中广泛推行裤子,后列国纷纷效仿。
但穿合裆裤,在当时仍旧只是士兵、猎户、农民等群体的专属,自恃高贵的贵族与士大夫群体们仍旧顶着得老寒腿的风险,穿着开裆裤。
当然,贵族们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不需要奔跑跳跃,对于他们来说,传开裆裤除了冬天有点冷,而且容易走光之外,也没什么其他问题。
可即便容易走光,也无法改变贵族们穿开裆裤的传统,反而,贵族们制定了一整套的行坐之礼来进行约束,以防止走光。
最典型的就是古人的跪坐,就是为了防止春光泄出,这种被称作“跽”的跪坐坐姿,虽然看上去会显得比较稳重端庄,但非常难受,尤其是长时间保持。
并且,古人除了淌水的时候,平时禁止无缘无故把裙子掀起来,这被视作不合礼的行为。
现代人伸开双腿坐在地上的坐姿,在古代被称作“箕坐”,也是不被允许的,原因自然是因为里面穿的是开裆裤,荆轲刺秦失败,荆轲就如此坐在地上,以表示对嬴政的蔑视。
古人对开裆裤,有种近乎成谜的执念从各项史料记载与现实出土文物来看,古人穿着开裆裤其实是与合裆裤基本齐头并进,大致上一起发展的,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开裆裤并非是因为缝纫技术不够造成,至于汉灵帝命宫女穿着开裆裤的说法,只不过是个例,何况古代传开裆裤,无论男女老幼皆是如此。
魏晋时代,开裆裤仍旧风行,直到隋唐时期,受到游牧族群文化的影响,合裆的裤子在中原开始广泛盛行了起来,这一时期,除了正式场合之外,上衣下裳的服制在男子群体之中逐渐减少了很多,人们日常也开始穿裤子。
然而到了宋朝,穿开裆裤的风气重新复苏,不过这一时期的开裆裤穿法看上去非常迷,因为宋朝的开裆裤是穿在合裆裤外面的,而这样的穿法,从宋朝一直延续到了明清两朝,直到清朝晚期仍旧还保留着这样的穿法。
明清时期,里面穿合裆裤,外面穿开裆裤,成为了当时显贵富人的一种标配,寻常人反而不会如此穿着。
而事实上,这种看上去非常怪的穿着,而且还是富贵群体的配置,也有其背后的道理。
最初,袴被发明出来就是为了保暖,宋元之前并没有棉花,所以用来制作足够保暖的袴需要非常厚实的皮料之类,所以其实穿起来也并不方便,后来随着时间发展,人们夏天也开始穿袴,但是又觉得太热,可不穿又会走光,所以富贵者会使用丝绸之类制作袴。
而到了天气冷的时候,穿着厚实的合裆裤用于保暖,为显富贵,再在外面套上一件轻薄华丽的开裆裤,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习惯,结果在后来,虽然棉花等新材料传入,纺织与缝纫技术进步,但民间却普遍如此穿着而不明就里。
合裆裤外穿开档,并没什么方便的地方,然而古人的有些习惯,确实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比如裹脚这样的风俗,很难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
可以说,古人传开裆裤,仅有最初是因为技术问题,然而合裆裤出现后数千年,古代的先民们仍旧保持着对开裆裤的迷恋,可能确实是因为文化传统习惯。